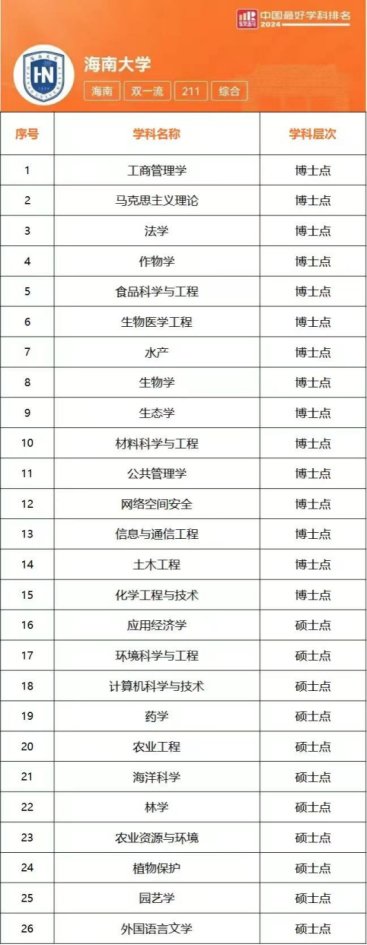我們常常為本民族的悠久歷史和豐厚文化遺產(chǎn)而自豪。但歷史遺產(chǎn)有時(shí)也會(huì)成為現(xiàn)實(shí)社會(huì)的沉重負(fù)擔(dān)。對(duì)此,魯迅早在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初期就已經(jīng)作過極為明晰、確定的表達(dá)。他在1918年發(fā)表于《新青年》的《隨感錄·三十六》中說:“而‘國粹’太多的國民,尤為勞力費(fèi)心,因?yàn)樗摹狻?,粹太多,便太特別。太特別,便難于與種種人協(xié)同生長,掙得地位”,“于是乎要從‘世界人’中擠出”。國寶、國粹雖寶貴,但要保住它,不但要付出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財(cái)力,而且還會(huì)造成國民心理的沉重負(fù)擔(dān),使他們難于匯入世界發(fā)展的新潮,最終會(huì)被擠出“世界人”的行列,成為落伍者。
時(shí)當(dāng)“五四”大潮,魯迅以開放的世界眼光,站在以人為本,以民族解放、復(fù)興為本的革命民主主義立場(chǎng)上,來審視、對(duì)待古老文明中國的物質(zhì)和精神文化遺產(chǎn)。他指出:“我們目下的當(dāng)務(wù)之急,是:一要生存,二要溫飽,三要發(fā)展。茍有阻礙這前途者,無論是古是今,是人是鬼,是《三墳》《五典》,百宋千元,天球河圖,金人玉佛,祖?zhèn)魍枭?,秘制膏丹,全都踏倒他?!保ā度A蓋集·忽然想到六》)不管是多么寶貴的東西,都必須讓位于人的生存發(fā)展、民族的解放復(fù)興。這一基本立場(chǎng)和整體思路,是不可動(dòng)搖、不容置疑的,貫穿在他對(duì)一切具體事務(wù)的評(píng)判分析之中。
在中華民族的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中,最為宏大、重要的莫過于被國人視為民族精神象征的萬里長城。長城的筑建,歷時(shí)甚為久遠(yuǎn)。《左傳》僖公四年(公元前657年):“楚國方城以為城”,是關(guān)于修筑長城最早的文字記錄。戰(zhàn)國時(shí)齊、楚、魏、燕、趙、秦、中山等國相繼興筑。秦統(tǒng)一后,又將秦、趙、燕長城連貫為一。此后,漢、北魏、北齊、北周、隋、明各代都有構(gòu)筑。僅明代洪武至萬歷年間,先后修筑長城便達(dá)18次之多。其總長約6700公里,是名副其實(shí)的萬里長城,由于歷代不斷修繕大部分至今仍基本完好。從《左傳》最早的記載,到萬歷年間,前前后后,修修補(bǔ)補(bǔ)了兩千多年!勞民傷財(cái)無算,在它身上附著多少孟姜女夫婦的冤魂和斑斑血淚。如果說古代長城的修筑,還起到了一定的防御外侮的作用,那么當(dāng)失去了抵御外族入侵作用之后,它便成為一種純文化意義上的物質(zhì)遺產(chǎn)。要維護(hù)“萬里長城永不倒”,擁有這份遺產(chǎn)的中華子孫,便要永無休止地付出沉重的代價(jià)。而長城,只不過是我們豐厚文化遺產(chǎn)中的一件。
魯迅早在1925年曾寫過一篇題名《長城》的雜感。他文章中關(guān)于長城的議論,定會(huì)使當(dāng)時(shí)和以后的保古家瞠目結(jié)舌。魯迅指出,長城這工程“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,胡人何嘗擋得住”!現(xiàn)在它已成為需要加以維護(hù)保存的古跡:“這長城的構(gòu)成材料,是舊有的古磚和添補(bǔ)的新磚。兩種東西連為一氣造成了城壁,將人們包圍?!彼钌罡惺艿介L城一類的文化古跡對(duì)現(xiàn)實(shí)中人的威壓和拖累,所以呼吁道:“何時(shí)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?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!”這種在今天看來有些過激的言論,正體現(xiàn)了“五四”時(shí)代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。
收藏國寶最多的莫過于故宮。1933年初,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北之后,又攻占山海關(guān),華北形勢(shì)日益吃緊。國民政府眼見北平難守,便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(huì),決定將故宮重要文物搬運(yùn)南京。從二月至五月分五批陸續(xù)南遷故宮古物共19560箱。魯迅針對(duì)國民黨當(dāng)局值此民族危亡之際,首先考慮的不是國土和人民,而是古董和珍寶的行為,作雜文《崇實(shí)》加以抨擊。他寫道:“倘說,因?yàn)楣盼锕诺煤埽幸粺o二,所以是寶貝,應(yīng)該趕快搬走的罷。這誠然也說得通的。但我們也沒有兩個(gè)北平,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(xiàn)存的古物還要古?!瓰槭裁吹蛊蚕虏还埽瑔伟峁盼锬??”1月28日《申報(bào)》號(hào)外報(bào)道了故宮古物開始起運(yùn),北平團(tuán)城玉佛亦將南運(yùn)的消息,翌日,該報(bào)又刊出教育部通電,譴責(zé)當(dāng)榆關(guān)告急之際,北平各大學(xué)中逃考及提前放假的做法為“妄自驚擾,敗壞校規(guī)”。魯迅敏感地從這兩則消息中看出了國民黨當(dāng)局重物輕人的立場(chǎng),便撰寫了雜文《學(xué)生和玉佛》,將這兩則報(bào)道放在一起,并作打油詩予以揭露、諷刺。
物質(zhì)文化是如此,對(duì)于精神文化,魯迅的立場(chǎng)和態(tài)度也是一致的。1925年《京報(bào)副刊》約請(qǐng)名流學(xué)者向青年推薦閱讀書籍,分“青年愛讀書”和“青年必讀書”兩種書目各10部。魯迅只寫了《青年必讀書———應(yīng)〈京報(bào)副刊>的征求》,回答道:“我以為要少———或者竟不———看中國書,多看外國書”。后來作者又對(duì)此作了解釋:“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,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,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,決不是聊且快意,或什么玩笑,激憤之辭?!?BR> 對(duì)人類文化遺產(chǎn)的認(rèn)識(shí)和態(tài)度,是一個(gè)嚴(yán)肅而重大的問題。魯迅對(duì)中國文化遺產(chǎn)問題,在其他許多文章中有更全面系統(tǒng)的論述。以上引文均出自其雜文。雜文寫作,往往抓住事物的某一點(diǎn)或某一側(cè)面,予以集中強(qiáng)調(diào),而不作面面俱到的分析。但從這些引文中,我們已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迅一以貫之的文化立場(chǎng)和觀點(diǎn),至今仍具有指導(dǎo)意義,值得深思。
從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至今已近百年,新文化形成了學(xué)術(shù)界所謂“五四傳統(tǒng)”?!拔逅摹毙挛膶W(xué)也已成為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(chǎn)留給后人。那么,它會(huì)不會(huì)也同時(shí)成為一種負(fù)擔(dān)?許多人會(huì)以為,這種提法很荒謬。但是,孰不知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。當(dāng)我們擁有一份遺產(chǎn)的同時(shí),我們本身也會(huì)為遺產(chǎn)所擁有。即以五四文學(xué)而言,許多現(xiàn)代作家都擁有廣大的讀者。不僅他們的著作需要編輯出版,而且為了紀(jì)念他們,許多地方還建立了某某現(xiàn)代作家的紀(jì)念館。如魯迅,僅大型紀(jì)念館,就有北京、上海、紹興三處。此外,凡他到過或工作過的地方如廈門、廣州、杭州等地,還建有一些中小型的紀(jì)念室或展室。建有紀(jì)念館的現(xiàn)代作家非止魯迅一人。統(tǒng)計(jì)起來,是一個(gè)不小的數(shù)目。但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界的研究者猶嫌不足。在尋訪現(xiàn)代作家足跡時(shí),常常會(huì)聽到這樣的感慨:“這是某某作家居?。ɑ蚬ぷ鳎┻^的地方,怎么可以變?yōu)槊窬樱ɑ蜣k公場(chǎng)所)呢?”如果照他們的想法去做,真不知若干年后,還有沒有活人居住的地方。且像魯迅這樣的現(xiàn)代作家,已經(jīng)成為許多學(xué)者終生研究的對(duì)象。也就是說,許多人要把一生貢獻(xiàn)給魯迅研究工作。不知魯迅如果地下有知,對(duì)此會(huì)有何感想?
包括新文學(xué)在內(nèi)的新文化,既然已經(jīng)成為一種“五四傳統(tǒng)”,它也就成為評(píng)判文化立場(chǎng)的一種標(biāo)準(zhǔn),一種不可隨意跨越的紅線。這樣五四文化遺產(chǎn),就不僅僅是我們創(chuàng)造未來文化的資源、基礎(chǔ)和前提,它同時(shí)也會(huì)成為一種心理的壓力。譬如魯迅作品的教學(xué)與研究,早已成為一個(gè)敏感區(qū),社會(huì)上政治、思想、文化等等的變動(dòng),都會(huì)在這一領(lǐng)域反映出來。魯迅作品在某些選本中篇目的增減變更,以及對(duì)作品意義的不同解讀,都會(huì)被提升到“綱”和“線”上來認(rèn)識(shí)。即如近來由人教社高中語文課本將魯迅作品減為三篇而引發(fā)的爭(zhēng)論,在媒體上形成輿論熱點(diǎn),搞得沸沸揚(yáng)揚(yáng),就正是這一文化心態(tài)的反應(yīng)。
本來,從語文教育的角度編選語文(也曾稱之為國文、國語)課本,在入選的古今中外作品比例上,以及哪些作家入選、入選多少,編選者見仁見智,自由的空間還是很大的。即使是魯迅作品,不斷調(diào)整入選的篇目和篇數(shù),以使其更適應(yīng)學(xué)生的理解、接受能力,更方便教師的教學(xué)活動(dòng),使課本更好地完成對(duì)學(xué)生進(jìn)行語文教育的目的,這都是很正常的。并不一定直接反映編選者對(duì)魯迅、對(duì)“五四傳統(tǒng)”的立場(chǎng)和態(tài)度。相反,在文革中,當(dāng)中學(xué)語文課本中差不多只剩下魯迅作品的時(shí)候,也正是魯迅被嚴(yán)重歪曲,“五四傳統(tǒng)”被徹底否定的時(shí)代。如果僅僅因?yàn)闇p少了幾篇作品,便作出“魯迅淡出中學(xué)語文課本”的結(jié)論,便急呼“中學(xué)語文課本中決不能沒有魯迅”,這未免把問題看得過于嚴(yán)重,把本來可以具體分析的問題上綱上線了。
隨著時(shí)代的發(fā)展和世界的開放,今后的中學(xué)語文課本的內(nèi)容、形式都會(huì)不斷變化。當(dāng)代人需要了解的新知日益增多,我們決不可以讓青年學(xué)生的精力過多地用于古人、逝者身上。包括魯迅在內(nèi)的新文學(xué)作家的作品,在未來中學(xué)語文課本中的比重,應(yīng)該減輕,而不應(yīng)加重,乃是順勢(shì)。這是站在魯迅當(dāng)年以人為本、以民族復(fù)興為本的文化立場(chǎng)上看問題所必然得出的結(jié)論。
如果我們?cè)僮岕斞赶壬_列一份“青年必讀書目”,我想,先生的在天之靈是決不會(huì)在“不讀中國書”之后加一個(gè)括弧:(魯迅著作除外)。其實(shí),魯迅生前對(duì)這個(gè)問題已經(jīng)作了回答。孫伏園1924年在一篇文章中說,當(dāng)魯迅得知《吶喊》被定為中小學(xué)生讀物后很反感,甚至認(rèn)為《吶喊》“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,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,也有不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”。